第五波疫情爆發對醫護人員、新冠肺炎患者和大眾心理健康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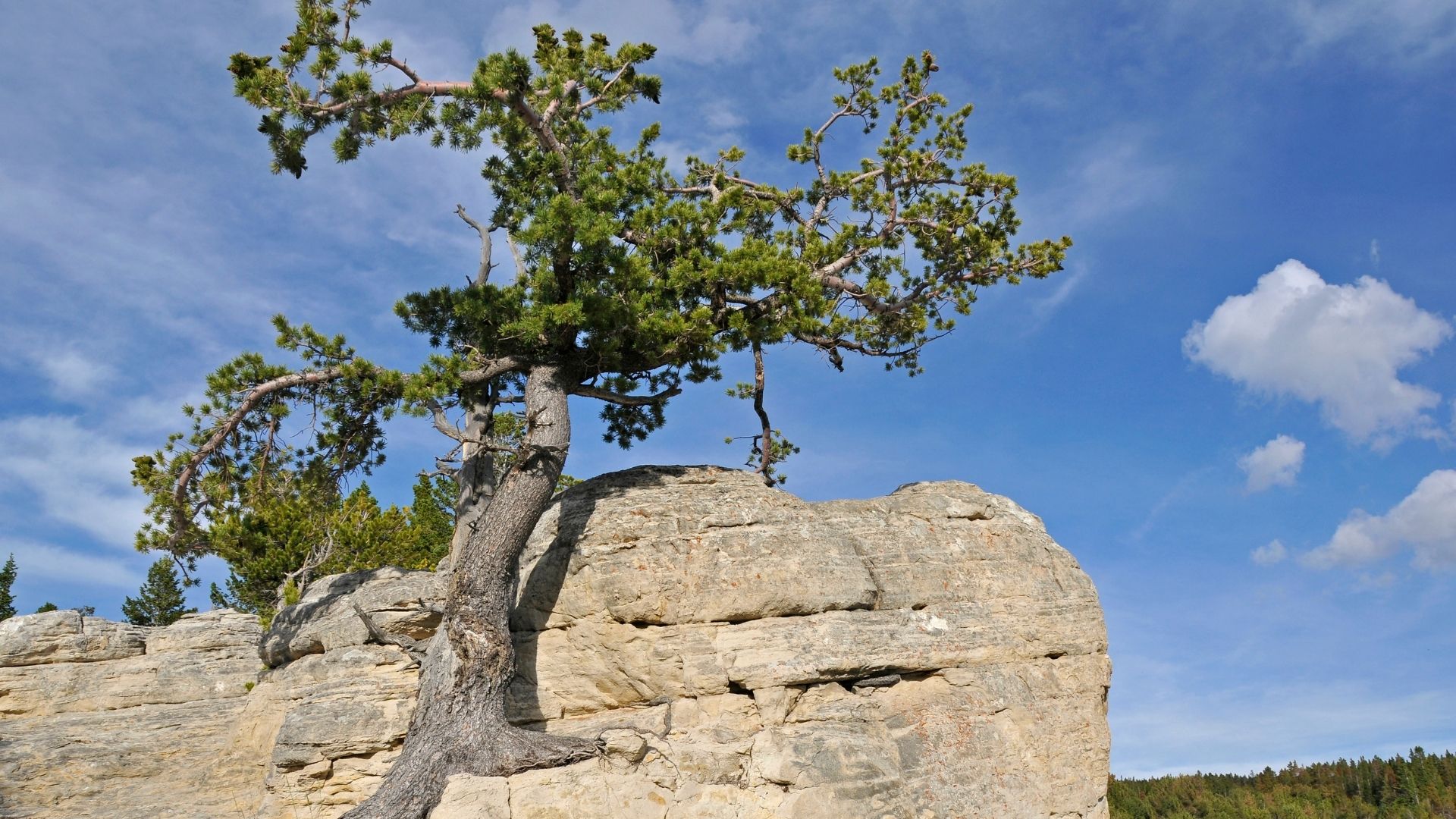
《紐約時報》於2月16日報導了一項於美國進行的大型研究,分析了接近154,000名的新冠肺炎患者,這些受訪者在受感染前都沒有患有精神病的紀錄或接受相關的治療。研究發現,對比那些受感染了的人和同一時期沒有受感染的人,大約39%的人更大機會被診斷患上抑鬱症,而約有35%的新冠肺炎患者在受感染的數個月後則更有可能被診斷患上焦慮症。
英國心理學家(Joel Vos)進行了一項有系統的綜合分析,就26 個針對新冠肺炎與心理影響的調查作出研究。在十多萬的受訪者中,超過六成的醫護人員出現急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症狀。另外,當中大約三分一人表示經歷焦慮和抑鬱的情緒,以及飽受失眠的影響(預先於 2020年發表)。他的綜合研究亦發現三分一的新冠肺炎患者和公眾人士都報告自己擁有焦慮、抑鬱、壓力和失眠的症狀。醫護人員、新冠肺炎患者和公眾人士可能會經歷什麼心理問題?
作為人類,我們很自然地渴望在生活中獲得控制感。但是,疫情實際上讓我們了解到生活是難以控制。這個事實令我們感覺受到威脅,並使我們感到焦慮。對於那些較容易焦慮的人,他們會更頻繁地反覆思考自己是否有可能受到感染或需要被送到隔離營。此外,他們也有機會非常擔心接種疫苗副作用、自己的經濟狀況不穩定和面對失業的可能性。當一個人愈是反覆思考自己的憂慮,便愈有可能導致他或她無法集中注意力在生活中進行有意義的活動,同時出現高度焦慮的症狀(如肌肉繃緊或心悸)。
不少人可能在疫情期間經歷損失,譬如是失去工作、失去親人、與親友減少了聯繫。此外,他們亦可能更頻繁地出現情緒低落的情況。這些人可能會開始對自我和自己未來的生活產生更多的負面認知。他們可能會認定自己是一個失敗者,而且沒有人會關心他們。此外,他們也有機會減少進行自己曾經喜歡而又富有意義的活動,以及失去與家人和朋友聯繫的動力。對於那些在疫情期間感到被孤立的人而言,他們可能會感到非常孤獨和絕望,當中有些人可能甚至覺得生活已經毫無意義。
那些受感染的患者,如果他們非常擔心自己患病的後遺症,可能會更容易患上焦慮症。在治療的過程中,他們可能在住院或隔離的期間承受不少壓力。對於那些病情比較嚴重的人,他們承受的痛苦可能會加劇了無助和沮喪。那些病癥比較輕微或沒有病癥的患者可以因為被送往隔離營而感到被孤立和孤獨,如果一個沒有應對隔離的策略,可以會增加他或她焦慮和反覆思考。
新冠肺炎患者的感染個案持續上升,加重了公營醫院的醫護人員的工作負擔。他們可能需要超時工作和處理病人的負面情緒,承受莫大的壓力。另外,這樣也增加了這些醫護人員染病的風險,加劇焦慮和抑鬱情緒。由此他們害怕自己會把病毒傳染給自己的家人,因此他們可能會選擇在疫情期間自我隔離。如果他們未能與重要他人聯繫,有機會感到非常孤單和疏離。
毫無疑問,第五波的疫情對我們的心理健康造成影響,並不只限於專業的醫護人員和受感染的人士。在這個時候,我們除了要注意身體健康,更加需要留意自己的心理健康。如果你發現自己的焦慮、抑鬱或壓力正在影響正常的日常生活功能,你可能需要尋求專業人士來獲得支援和接受心理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