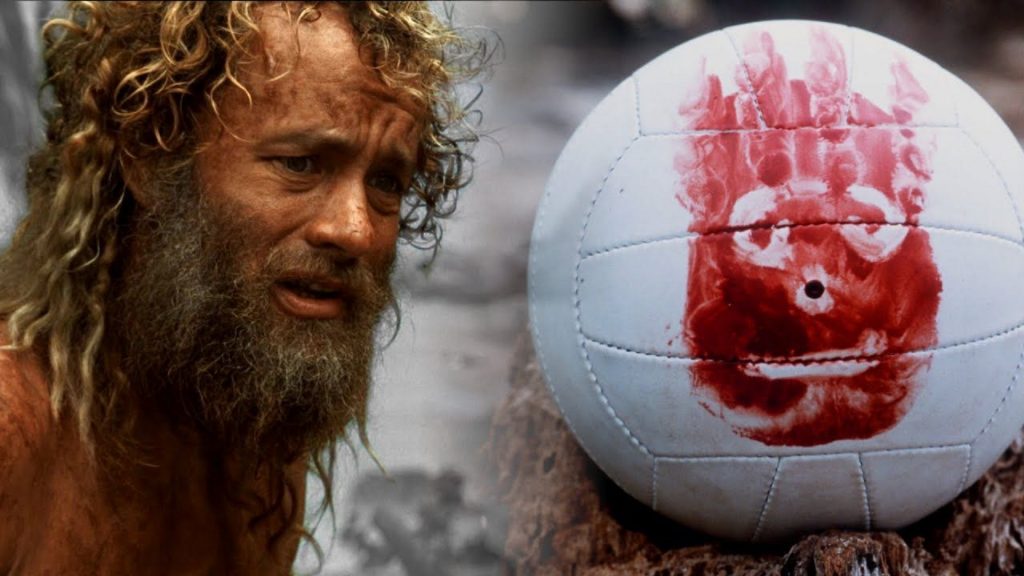对抑郁状态感到挣扎的恶性循环

尽管越来越多人觉察到对精神疾病去污名化的重要性,但是人们仍然很难接受抑郁发作的时刻。相反,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精神健康状态不错或整体上感到快乐而「自豪」。他们可能认为自己在保持心理健康方面做得很好。当然,一个人对自己处于良好状况感到满意并无不妥。然而,当一个人无时无刻致力保持「愉快的心情」,他或她可能难以面对生活中无可避免地出现情绪起伏的情况。我的其中一位求助人最近陷入抑郁状态,更因为抑郁情绪而感到非常不适。每当她和家人或朋友交谈并觉得对方过得很好或生活美满时,她就会感到很强烈的自卑感。她认为其他人一定会因为她的身体状况不佳而批评她。于是,她开始疏远别人,以及对自己持续情绪低落感到无助。与此同时,她无法为自己制定任何活动计划,如未能到健身房跑步或进行静观练习。无论她如何努力尝试坚持自己的计划,但都未能做到。面对这些处境,她感到更加沮丧。
我们可能很容易觉得长时间过得很好和生活幸福美满是很「特别」。如果我们的生活很好,似乎别人会觉得我们与别不同,或是显得更为优越。这种视自己为一个特别的人的渴望有机会使我们被困于错误的自我意识,并令我们不太可能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联系。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向别人展现自己的全部,这种带有幻象的自我意识在我们和他人之间筑起了一道墙。
当我们与他人互动时,如何能够展现更多的真实性?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进行静观练习,并且更为关注我们每时每刻的思想。每当我们记起的时候,就需要把自己的意识带回我们的呼吸中。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细心留意自己的脑海是否有任何念头升起。例如,当有人对我所写的东西给予正面的回馈时,我会尝试把自己的意识带回我的呼吸上。我可能会觉察到自己内心渴望变得「伟大」或「特别」。这样,我可以对自己说:「我留意到自己有这种渴望。」当我们能够更加观察内在的自己时,就可以打破自己和他人之间的那道墙。这是因为我们将注意力从关注自己有多「特别」转移至社交互动或别人想向我们传达的讯息上。
还有一点是,我们很容易陷入渴望放下带有幻象的自我意识的陷阱。事实上,我们有机会坠进渴求「无我」的陷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或许需要放松,做当下的自己。
同样地,如果我们感到抑郁,或有机会非常渴望尽快摆脱这种抑郁的状态。我们需要练习放松,并对自己目前处于抑郁状态培养自我慈悲。如果我们停止挣扎,也许就能逐渐摆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