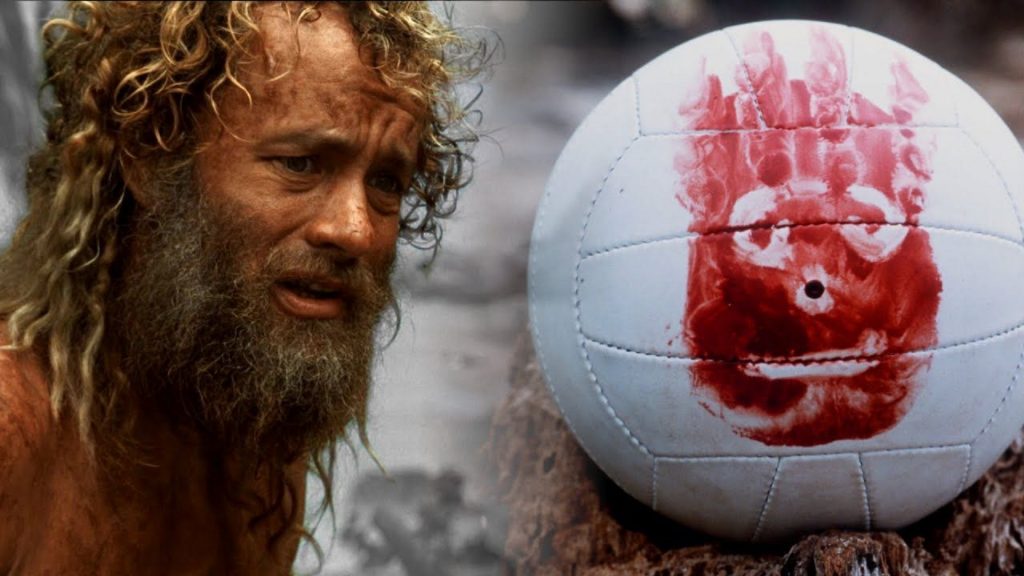为什么有些人总是重复地与自恋型人格的人交往,并被困于关系中?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反复地与具有自恋型人格特质的人交往,甚至一次又一次陷入虐待关系中。我的其中一位求助人被困于与具备这种特质的男士建立的亲密关系中。从表面看,她的男朋友用心关注她在生活上的每个细节,并且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譬如,他每天都会陪她上下班,还会为她支付所有的账单和负担每月的日常开支。在购物时,他亦会为我这位求助人选购衣服或眼镜的款式。每当我的求助人没有按照男朋友的建议,以及对下决定有个人意见时,她的男朋友都会狠狠地批评她的选择,希望借此让她顺从他的意思。她的男朋友经常在生活的各方面批评和贬低她,比如外貌、工作能力和智力等。例如,如果我的求助人被行销人员欺骗了,他会对她说:「你真的很愚蠢!怎会不知道这些是行销策略?为什么你会作出那么糟糕的决定?」渐渐地,我的求助人变得越来越自卑,甚至害怕在生活中作出任何决定。尽管她的朋友劝喻她考虑与男朋友分手,但是她仍然觉得自己非常依赖他,并认为她的朋友建议她作出一些不利自己的事情。在进行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曾多次与具有类近特质的男性约会。如果没有和我讨论,她自己可能未曾觉察到这种模式。为什么有些人会反复地与那些有机会虐待他们的人约会?
人们之所以反复地选择具有自恋型人格特质的伴侣,其中一个可能性是他们有机会曾经被一或两个自恋型父母虐待过。结果,他们倾向于选择具备类近特质的伴侣来寻求解决创伤的方法。由于经历童年创伤,他们可能会有持续低自尊的问题,并需要具有相似特质的人来认同他们。这些人可能下意识地认为只要获得这类型的伴侣的认可,就能克服童年创伤和解决相关的问题。例如,上述的求助人非常努力地保持理想体重和完美无瑕的皮肤,以寻求有自恋型人格倾向的男友的认可。尽管男朋友一直不断地批评她的外表,但实际上她认为自己有机会获得男朋友的认同,并相信这样就足够了。
矛盾的是,部分经历童年创伤的人即使重复地受到自恋伴侣言语甚至身体虐待后,仍然会选择与对方保持关系。这些人在面对伴侣对他们作出虐待行为时,可能经常感到无能为力。在他们小时候,就算父母对他们做了一些残忍的事情,他们亦无法离开虐待他们的父母。作为子女,他们需要依靠父母才能满足生存需求。有见及此,他们最需要做的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被父母遗弃。在某些情况下,孩子可能会为了生存而脱离自己被虐待的现实,需要在精神上摆脱其父母的虐待行为。结果,当经历童年创伤的人在成年后与自恋者发展浪漫亲密关系时,他们有机会产生解离性防御。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否认、最小化或从对建立理想关系的幻想中抽离。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感觉不到他们的伴侣于当前的亲密关系中正在虐待他们。
如果你或你的朋友似乎陷入与自恋伴侣的虐待关系中,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够反思自己的关系模式,以及学习采取必要的行动来避免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境。如果未能确定当前的关系是否属于虐待关系,与朋友或心理治疗师交谈是有益的,并更有机会就关系模式进行反思而找到出路。